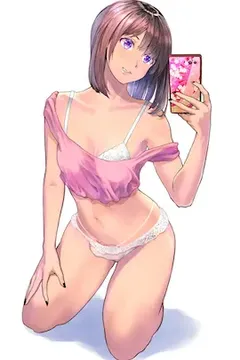梅素后来才明白,性格与行动相辅相成,不同的职业塑造不同的处事方式。
曾经,梅素的身份是学生,刚毕业就嫁为人妻,闲散度日,自然满脑子情爱。
如今,她是一名厨房的初级学徒,但性子从温吞犹豫,变得精明爽利了不少。
说是学徒,其实也是自谦。
在完成巴黎蓝带的传统法式甜点技法与西点管理课程后,梅素拼尽全力争取到一家星级酒店的糕点房实习机会。
那段时间收获颇丰,小腿却不堪重负。
若非她每晚坚持按摩缓解,静脉曲张这个职业病就要早早找上门来了。
因此,三个月实习期满,梅素就利落辞别,转入一家米其林三星退休主厨创办的私厨,负责甜品准备工作。
但这份经历也不长,只维持了八个月。
因为她的恋人尚崧在完成宗赵两家合作的监督事务后,申请调驻巴黎参与军事医疗数据跨国法规整合项目。
任期结束后,他又在尚家出面协调下转赴新西兰,接手外交事务部门的相关职务。
两人在巴黎同居满一年,符合事实伴侣条件,尚崧就顺理成章为梅素申请了外交人员家属签证。
在主厨的祝福与几箱打包好的锅碗瓢盆陪伴下,梅素精简行李,随尚崧一同奔赴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悠闲国度。
日子确实如她所想象的自由自在。
梅素研究惠灵顿本地的创业政策,结合手头剩余资金情况,开了一家烘焙工作坊。
启动资金她占40%,余下靠社区银行贷款与女性创业机构提供的补助。
工作坊低调运营了一个YouTube频道,每半月发布一条甜品制作教学视频,不紧不慢地介绍她认为适合新手尝试的食谱。
影片画风不算精致,连BGM也没有,顶多是开头时和观众打个招呼,居然也吸引了好些学员实地参与短期课程。
无课时,她每日用时令食材做糕点售卖,卖光是常态,剩几个便进了尚崧的胃。
在新西兰,同居是一种合法的关系形式。
他们没有登记结婚,感情也稳稳当当。
毕竟,合力经营生活,便足以构建信任,彼此绑定。
梅素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婚姻就拒绝接纳新的爱人,但总以为自己多少会将曾经的创伤记得清楚。
然而,在年长五岁的尚崧温和绵密的爱意包裹下,她慢慢发现,藏在旧伤口中的负面情绪除了折磨自己,也别无大用了。
放下过去,并不等于否认曾经的自己。
梅素愿意在生活的小雪崩过后,攥住尚崧递过来的手,再踏上爱情这条路。
他是她的第二次心动,却让她第一次明白——未必需要山盟海誓,也可携手共赴新生。
尚崧不擅长浪漫,风花雪月少有,却用温火慢炖的长情照拂把她重新养了一回。
他不会将煽情的“我爱你”挂在嘴边,却会说“待会我送你去工作室,刚看天气要下雨”。
他不会信誓旦旦保证“宠你一辈子”,却会在忙碌一天后带回她近期钟情的小零嘴,洗净后放到桌头温声叮嘱。
“上一批杏子酸,别吃了,我换一箱。”
在这些克制妥帖的照料中,梅素对高门后代的刻板印象再次打破。
显赫出身的尚崧,没半点公子哥气。
尚家扎根军政多年,是南部战区最早一批红色家族。
少将父亲尚有台自小带他进军营锤炼性子,艺术基金会董事母亲席兆珂开明爽朗,两相中和,加上国关院的战略安全专业背景,尚崧寡言稳重,又细腻周全。
这样的尚崧,是她走了人生弯路后,豁然开朗邂逅的沉默的山。
他可以在任何境况接住她,也撑得起生活的重量,把看似漫长的一生掰成年月日、时分秒。
日子细水长流,也有温甜蜜意。
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梅素如今看尚崧的一举一动自带滤镜:他套着卫衣扛十公斤特价土豆回来时的背影很帅,爬上屋顶清理雨水槽的身手敏捷而靠谱,周末开割草机修理草坪也比开跑车更性感。
他们每周固定去趟大型商超采购日用品和食材,闲暇时也会踩着单车去本地农夫市场挑选新鲜蔬果,促销季节更是全副武装扎进卖场凑个热闹。
坐落于Khandallah的1.5层小别墅在这琐碎日常里,被一点点收拾得像她在港城住过的那间度假木屋,静谧、自在,是家的模样。
再后来,他们领养了一只边牧,叫Dorothy。
四季三餐,两人一狗,也不失为一种行动派浪漫主义。
从米其林晚餐到特价南瓜,从私人会所到周末有机市集,从冬季Treble Cone滑雪到夏日农场摘蓝莓。
生活变得具体,爱人也变得真实了。
岁月安稳,梅素却暂时不考虑与尚崧孕育后代。
尚崧上有大哥下有小妹,家族开枝散叶无需他操心。
席兆珂在偶尔视讯时,看着二儿子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伴侣,笑得像终于把滞销货卖出去一般。
“孩子不是必选项,你俩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就是孝顺我了。孙子孙女那是bonus,不是KPI。”
得了这句,梅素便放心了。
况且,她始终未有足够的安全感和认同感来接受母亲的身份。
留在赵家的赵侗,从几个月的婴儿期起便与梅素形成固定视讯的习惯。
偶尔背景会传出赵壬叨叨地给赵侗念书的声音,或者徐鸣岐与莫用仪的低声交谈。
赵家把赵侗抚养得玉雪可爱,口齿伶俐,多数时候叫她姐姐,也挺好。
梅素虽缺席赵侗的成长,却也会安排适合的见面时机。
四岁时,赵侗随姐姐赵壬与Eden,在前大伯哥赵赐和助理团的带领下,趁春假来惠灵顿玩了。
三小只活力充沛,遛得梅素的牧羊犬Dorothy也腿软气喘。
想起那短短半个月有欢笑有汗水的相处,梅素窝在尚崧怀里心有余悸,低声嘟嚷。
“我宁愿搓十个小时酥皮,也不想在外面晒着太阳跑三小时。赐哥是真有精力和爱心啊。”
窗外月色明亮,映得尚崧冷峻的面容柔和了几分。
他调整了下梅素侧躺的姿势,让她更好入睡之余,还能顺带捏捏她的手放松肌肉。
“每个人都不同,你这样很好。”
他的安慰很简短,也从来不要求梅素要成为怎样的人。
梅素哼笑一声,抬手揉搓他那张英挺的脸庞,又挑衅地拨弄他的睫毛。
“噢,我什么样都行?”
“嗯。”
“你真奇怪。”
梅素掐得他耳朵通红,又旧事重提。
“你以前每次见我,我要么吐得像个疯子,要么把你衬衫抠烂…你是受虐狂还是白骑士?”
问题很尖锐,但尚崧习惯了。
梅素被他养得什么话都敢说,跟以前怯懦柔顺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素素,我们很像。”
“哪里像了?”
“你想依赖人,又不敢说。我也是。”
梅素来了兴致,撑着他结实的胸膛半坐起身,长发扫过他的脖颈。
“那天你扶我,我说谢谢,不是很正常?”
尚崧笑笑,纵容地将她的头发掖回耳后,才把手落回她腰间轻柔摩挲。
“你是说‘麻烦你了’,还问我茶水合不合心意。那时,你明明不开心。”
她说的话被记得一清二楚。
而尚崧那日的距离感也不是因为天性冷淡,只是作为家中次子,习惯了将情绪藏得比谁都深。
梅素喉间哽咽了一下。
眼前这个沉默少言的军官,其实温柔得内敛。
梅素的鼻尖酸涩,瓮声调侃他。
“我当时以为你是个喜欢怀孕人妻的变态来着。”
尚崧笑得胸膛震颤,眸光却始终清和。
“那时的你,已经决定不要那个身份了,不是吗?”
是啊,梅素虽然性子温吞,但在创伤事件到来时,也敢接受、思考、放下。
她抿出乖怜的梨涡,眸光盈盈,似陷入回忆。
“以前的我,说得好听是随遇而安,难听么,就是窝囊。”
“但我还小嘛,总会长大的。”
尚崧抬手,指腹擦去她眼尾的一点湿润,捧着她柔嫩粉润的脸庞细细打量,缓声下结论。
“嗯,素素长大了。”
“现在的素素拿得起刀,扛得住15kg装的面粉,摘得了果子……”
明明尚崧是用平和的语调讲述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小事,却夸得梅素羞红了耳尖。
恋人的称赞,是来自天国的颂歌。
她无意识蜷紧了手指,不小心刮过了他的乳尖。
尚崧的身子一颤,低喘清冷又蛊惑。
“唔……”
昏暗中四目相对,不知谁先凑近,唇舌搅缠,缱绻厮磨。
衣衫尽褪的窸窣声和止不住的闷喘娇吟间,是有情人的呢喃私语。
“我摘的是你这颗果子吗?”
“不好吗…很湿了…让我进去…乖乖……”
“…呀…轻点…嗯…蛮人……”
“素素一直在吞我…真可爱……”
“变态…呜…你就是个变态……”
“哪有陪两年才换来名份的变态?”
“嗯啊…别顶那里……”
“要叫我什么?”
“唔…长官…啊啊…”
“这就高潮了?”
“… 我错了嘛… 崧哥哥……”
“再给你一次机会。”
“呜呜… 老公… 老公… 疼疼我……”
“这就对了… 素素,多些依赖我… 知道了吗……”
“嗯… 嗯……”
“要怎么做?”
“今天,明天,下一年… 我们都在一起……”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