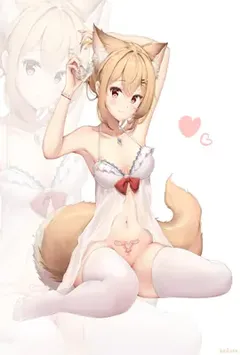那一页我们的关系确定下来我们决定就这样过
主卧的门紧闭着。
那扇门后,是属于眉眉和陈武的世界。而我,睡在曾经的客房。墙上是我和眉眉曾经婚纱照,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庭新的权力结构与亲密关系。
房间里的气息变了。以前属于客人的疏离感被迅速驱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强烈个人色彩的、属于“母亲”的掌控与关怀。
“你以前的床品和内衣物都太老气了,看着沉闷。”妈妈眉眉某日进来,身后跟着人抱着几个精致的购物袋,语气轻快而不容置疑,“你现在是妈妈的儿子了,一切都该焕然一新,看着就有好心情。”
于是,我灰蓝色的商务风床单被换成了卡通图案,质感高级,设计感十足,但也确实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
衣柜里,那些穿了多年的纯色平角裤,被替换成了设计更修身、色彩更明快(或许是宝蓝、暗红或带有细微时尚印花)的款式。
这并非矮化,而是一种基于她自身审美和年龄认知的强势更新。
她认为自己尚且年轻靓丽,她的“儿子”自然也不该是一副暮气沉沉的样子。
这一切的改变,在她看来,是让这个新家、以及我们的新关系,看起来更加和谐、时髦、充满生机。
“这样多好,”她打量着焕然一新的房间,满意地点点头,眼神里是一种纯粹的、对自身品味得到执行的愉悦,“看着就舒服。刚子,喜欢吗?”
“喜欢,妈妈。”我回答道。这种“喜欢”里,混杂着对她审美的顺从,以及一种通过接纳她的安排来取悦她的本能。
她越来越习惯以母亲和女主人的角色来使唤我,语气自然又亲昵。
“刚子,去把妈妈的披肩拿来,就香奈儿那条。”
“刚子,咖啡好了,给爸爸送一杯到书房去。”
“刚子,过来帮我看看这两个颜色哪个更衬我?”
爸爸陈武大多时候只是冷静地看着。他很少直接命令我,更像是一个最终的权威象征和妈妈权力的默许者。
他会在我为妈妈递上披肩时,很自然地对她说:“你这儿子,倒是细心。”他的话像是随口一句评价,却再次夯实了我的角色。
妈妈则会笑起来,那是一种被侍奉得恰到好处的愉悦,她会很自然地接话:“那当然,我眼光好嘛。”然后,她会顺势强调:“刚子,光细心可不够,更要懂事,听爸爸的话,知道吗?”
“知道了,妈妈。”我总是低声回答。
我无比怀念过去肌肤相亲的亲密,但那扇主卧的门,如今对我紧紧关闭。
没有他们的召唤,我绝不能踏入一步。
这是妈妈立下的规矩,语气温柔却毫无商量余地:“刚子,你是大孩子了,要知道分寸。爸爸妈妈需要私人空间,明白吗?”
“明白,妈妈。”
门内偶尔传出的细微声响,依旧会让我心脏紧缩。
但更多的时候,我穿着她为我挑选的、款式年轻的内衣,躺在她为我更换的、充满设计感的床品上,感受到的是一种被重新塑造后的、扭曲的安宁。
我的世界变小了,边界却异常清晰——就是这套公寓,就是以她的喜好为准则,就是以让他们满意为目标。
地暖很暖,新床品很柔软。
主卧的门,依旧紧闭。
而我,在这个被她审美彻底改造过的空间里,努力扮演好她所需要的那个——“年轻”、“时髦”、“懂事”的儿子刚子。
妈妈眉眉迅速进入了角色,一种混合着情人、未来主母与过度关怀的母亲的角色。她的注意力,很大一部分倾注在了即将高考的陈武身上。
“刚子,”她一边将保温盒装进印着可爱图案的布袋里,一边吩咐我,“你爸爸最近复习辛苦,我炖了虫草花鸡汤,你中午给他送到学校去。哦对了,给你小佳也带一份,你也喝点上班也累。”
“好的,妈妈。”我接过袋子。我知道,汤的口味是严格按照陈武的喜好来的,清淡少盐。我和小佳那一份,只是顺带。
大多数情况还是周五傍晚爸爸回来,周五的傍晚,像一种固定的仪式。
我会提前向单位请假,将车停在一中不远处的街角。
看着那些汹涌而出的蓝白校服身影,然后,看到他——陈武,我的“爸爸”,背着塞满试卷和梦想的书包,脸上带着一周苦读后的疲惫与一丝回家的松弛。
他拉开车门,坐进后排,习惯性地将书包放在一旁。
“走吧。”他言简意赅,目光甚至很少在我这个“司机”身上停留。
“好的。”我发动车子,驶向那个对于他而言是“爱巢”,对于我而言是“岗位”的公寓。
妈妈眉眉在这一天,总会显得格外不同。
一周的守候和电话里的绵绵情话,终于迎来了实体。
她会提前准备好一桌他爱吃的菜,口味清淡而精致。
家里的氛围会因为他的归来,而从一种等待的静谧切换成一种紧绷的活跃。
“武儿,累不累?喝点汤。”
“刚子,把爸爸的行李拿进去。”
她的指令围绕着他们二人,高效而自然。
晚饭后,主卧的门通常会早早关上。
里面会传来他们低低的交谈声,眉眉温柔的笑声,还有……一些别的声响。
起初,那是一种酷刑。
当我独自躺在客房的床上,耳边捕捉到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妈妈那压抑却又幸福而娇柔的呻吟时,全身的血液都会瞬间冷透,又立刻烧灼起来。
嫉妒、屈辱、痛苦会像海啸一样淹没我。
但渐渐地,一种可怕的习惯开始养成。
这种声音,连同周五接他回家的任务、手洗他校服的过程、喝同一锅汤的瞬间……都变成了这个新家庭结构里不可或缺的背景音。
它像一根针,反复刺痛我,提醒我她的身心完全属于另一个男人;但它又像一种扭曲的认证,认证着这个家的“正常”运转——看,爸爸妈妈是相爱的。
甚至,在这种持续的、缓慢的折磨中,我竟然能剥离出一种病态的慰藉:她听起来是快乐的。而她的快乐,不就是我最终极的奉献目标吗?
这证明了我所牺牲和忍受的是“有价值”的——我维持了能让她如此快乐的环境和关系。
这声音,和周一至周五她守着电话的温柔低语一样,都是她爱意的表达,只不过我听到的是更极致的一种。
我仿佛以一个卑微的视角,窥见了她生命中最饱满的热情。
于是,周五夜晚的主卧声响,于我而言,变成了一场持续的情感凌迟,也是一场献祭式的修行。
我穿着她为我挑选的、并不幼稚但完全符合她审美的睡衣,躺在她为我换上的、质地柔软的新床品上,在隔壁隐约传来的、属于别人的亲密交响曲中,咀嚼着那份名为“奉献”的苦涩幸福。
我知道这不正常。
但我已深陷其中。
周一到周五,我是她电话情思的旁观者,是她生活起居的侍奉者。
周五到周日,我是他们亲密世界的守门人,是那幸福声响的被动接收者。
这就是我的生活。
痛苦,却又让我感到一种被需要的、扭曲的平静。
听着隔壁隐约的声响,心中充满了痛苦、嫉妒、屈辱,以及一种巨大而扭曲的、名为“幸福”的平静。
我知道这不对。
但我需要这种“幸福”。
没有它,我活不下去。
一份,是同样的配方,或许是她母爱泛滥下一点顺带的、普惠的关怀。
但当我坐在车里,打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保温桶,喝着和她为陈武精心熬煮的同一锅汤时,一种可悲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看,我和他,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同一个来源的“爱”。
这让我感到一种病态的连接与满足。
这种幸福感还来自于——我的儿子,小佳。
他已经完全搬进了秋萍家,乐不思蜀。
秋萍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几乎填补了所有母爱的空缺。
我偶尔打电话过去,能听到他在背景音里和同学打游戏的欢笑声。
更让我…感到复杂又“欣慰”的是,小佳对于我现在的处境,竟然表示理解和高兴。
“爸,妈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啦!陈武哥…呃,你爸爸他挺厉害的,你跟着他们,我也放心。”他在电话里这样说,语气轻松,甚至带着一点如释重负,“你自己愿意就好。”
“你自己愿意就好。”
这句话,像一道特赦令,奇异地赦免了我内心深处的羞耻感。
连我的儿子都接受了,都认为我是“愿意”的,那我还有什么可挣扎的呢?
这仿佛为我的所有行为找到了一个最合理的出口——是的,这是我自愿选择的生活,我在其中感到了“幸福”。